对科研方向和技术路线的选择判断,需要系统深入的调研和周密的分析,还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技术支撑,这样才可以进行方向的凝练及准确判断,总之必须踏踏实实。
在可预见的未来,汽车不仅不会被替代,反而会是技术集成度最高的高新技术产品。

1977年参加高考前,他已在安徽省滁县琅琊山铜矿做了快三年的汽车修理工。“因为车子修得多,对车的基本结构比较了解,加上以前推荐上大学是干什么就推荐去上什么专业,所以填志愿时首选了汽车”,就这样,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专业成了赵韩高考第一志愿。
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赵韩留校任教,1987年公派出国到丹麦奥尔堡大学机械系机械学专业学习,自拟了博士论文课题《凸轮机构的专家系统与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CAD/CAM)集成系统》,1990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当时很多人选择留在海外,虽然国内办公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不能辜负国家的培养,故选择回国发展。”1999年,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2016年更名为机械工程学院)成立,赵韩是首任院长。如果说赵韩与汽车结缘源于他的工厂经历,那他与新能源汽车的深交是在成为院长之后。
浪尖“万亿之城2030”课题组于2025年7月4日在合肥工业大学与赵韩教授进行了两小时的交流,包括技术路线选择,校企合作模式,AI时代汽车教育的人才教育培训,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
赵韩教授核心观点有:技术路线选择很重要,判断要有技术支撑,“必须踏踏实实”;产学研合作首先要把事情做起来,对于高校来说,原始创新不能丢;汽车的带动能力会更大,应用场景范围会更广,产业链会更长,“汽车永远是高新技术产品,技术集成度最高的产品”。
澎湃新闻:2001年,电动汽车被列入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12个重大专项之一。你们对电动汽车的研究早于国家计划。
赵韩:当时学校穷,学院成立后基本就揭不开锅了,教师的奖金和课时酬金都要靠学院自行创收。创收就靠办成人教育班。我们找了很多方法只拿到了一点资源,装修了一些教室,招了计算机的成教生,才维持了局面。当时招了100多人,但所有精力全在这上面,本科生的课都没人上。
我向学校建议按照学生人数拨款给学院,而不是按教师人数。学校真的改了政策,一个本科生拨800元到学院,一个研究生拨1100元,这样学院才有精力做科研,抓学科建设。
虽然汽车专业历史老,但是确实太穷,安徽省没钱,分管学校的机械部也没钱。学院的条件差,设备绝大多数都是1950年代公私合营时候留下来的,所以我们搞科研需要另谋出路,换赛道。我看了很多学术学科学术研究资料,且当时国际上对化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讨论很热,觉得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当时刚刚起步还没人线年我就把学院汽车专业的主攻方向定在了新能源汽车。
对科研方向和技术路线的选择判断,需要系统深入的调研和周密的分析,还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技术支撑,这样才可以进行方向的凝练及准确判断,总之必须踏踏实实。
起初学院的教授们对这个方向持保留态度,所以当时只能带领年轻人先开始尝试。当年,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代纯电动轿车的研发。
赵韩:2001年国家“863计划”把新能源车列为重大专项,我们前期有了一些工作基础,就开始筹备去申请,找了江淮、奇瑞想联合申报。方云舟(哪吒汽车创始人)刚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奇瑞上班时间不长,他联系我表示愿意参与,我们就一起准备材料申报。我们申报的是混合动力轿车项目,当时同济大学、清华大学都在做氢燃料车,但我认为纯电动是长久的发展趋势。答辩表现不错,但因为奇瑞当时还不太被国家认可,故项目只给立项,没有给经费。该方向立了4个项目,两家给了经费,另外两家给予立项,如做得好,后面再给经费。
我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完成样车开发,整车可以正常行驶。科技部两次派员检查,时任科技部长本人也来了两次。当时,其他几家企业基本上还没有启动项目,因此我们的成果在部里引起了较大关注。从这一个项目开始,奇瑞才被逐步视为自主品牌企业,之后也获得了较多的经费支持。
2003年我们自主研发了二代纯电动车。当时合肥昌河汽车公司推出一款小型面包车,造型实用,空间也大。我自己买了一辆,使用铅酸电池,把它改成了纯电动车,一次性可以开100多公里。2005年到2006年,上海有几家企业主动联系我,希望和我们合作开发氢燃料客车。有一家超级电容公司,一家燃料电池企业,还有上海公交系统的相关单位,由于价格没谈拢,没能合作。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是继续推进项目,并与安凯合作。我带了几个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开发出了性能好的使用超级电容的安凯燃料电池大巴。原计划将该车用于2008年的奥运会,但因氢气瓶压力不足、成本高,加氢站建设审批复杂,不可以进行必要的试验,故无法推入奥运会。
其后,作为(安徽)省政协常委,我提交了支持安凯研发新能源汽车的提案。提案批到省科技厅后,我带副厅长参观安凯,介绍了新能源汽车情况。当时燃料电池成本极高(每千瓦约1万美元),使用贵金属减少相关成本很难,产业化前景比较远。省科技厅最终拨款50万元支持安凯。基于此,安凯开发了纯电动客车,因此安凯也是较早进入这样的领域的企业。
2009年,国家推出示范项目,因为我们从始至终和奇瑞联合承担国家863技术项目,且奇瑞和科技部的关系也比较好,于是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奇瑞联合申报芜湖市为示范城市,但由于芜湖科技局有关人员不得力,耽误了时间。其后我们联系了合肥市科技局,得到了该局和市主要领导的全力支持,把安凯、国轩、江淮、公交公司等都拉进来了,故顺利申报成功。我们撰写了申报书和示范城市的规划,合肥市按此规划推进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仅全国第一条纯电动客车的公交线路)运行很好,也很快在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赵韩:刚开始合作,就想把事先做起来,之后合作也有项目,比如联合申报、获得经费。
赵韩:现在汽车大多数都很强,有钱、有人才、有资本,学校在这方面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学校的特长就是早期引领,因此教育应该注重创新和发散思维。政府现在支持的主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需要支持高校等开展未知的前瞻性探索,为十年、二十年后的新产业提供可能的来源。
澎湃新闻: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公益的,捐钱,你们校友捐赠多吗?另一种是比较商业的合作。你们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韩:我们学校公益捐赠比较少,最近稍微大一点,但主要还是商业合作,就是企业出钱我们帮着处理问题、转化成果。我觉得校友捐赠会慢慢多起来,美国很多高校都是以校友和社会捐赠为主,政府出的钱比较少,我觉得这是未来一种可能的发展渠道。
澎湃新闻:在这次的调研中,从政府到园区,再到企业,都反复提到合肥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为汽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赵韩:我想可能有这几个因素,一是学校的定位始终是希望培养工程师、工业报国。二是学校学风比较好,学生学得比较扎实。三是师资水平比较高,教师能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更新教学内容。四是我们比一般学校学分要多,学业压力比较重,学生能吃苦。五是学生素质总体比较高。六是学校工科非常齐全,和行业、工业、企业联系比较密切,学生一直去企业实习。
澎湃新闻:您觉得汽车教育的方向是什么?复旦、交大都成立了和AI相关的学院。
赵韩:我始终觉得本科生教育应该是培育学生的学习能力,研究生教育是培育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很多人说本科学好多课程没有用,我认为这在每个专业都是必然存在的,甚至很多毕业生都转行了,关键是看这些课程和教学是否帮你建立了知识体系,提升了你的学习能力。研究生培养的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是工作任务或科研项目,往往不是依靠一个人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而是要学习新知识,并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去解决。
大学教育要根据社会需要来变。就拿汽车专业教育来说,汽车产业发展快、变化多,汽车教育在这方面压力一直比较大。早期我国比国外差距大,要考虑怎么加速追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汽车和路连起来,要车路协同;现在新能源汽车加智能化,更拓宽了汽车教育的内容。汽车要重新定义,过去汽车就是一个交通工具,现在的汽车已经超出交通工具范畴,成为万物互联的重要节点。因此,对于大学教育来说,现在不仅要面对知识大爆发,更重要的是AI出来之后教育方式要进行大的改革。随技术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周期很短,这就导致一些专业和实际的需求有比较大的差距,要一直变革。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大学教育有几个方面很重要。第一,鼓励高校去探索新的东西,引领行业。企业再重视技术探讨研究,也不会跨行去做新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关注自己的领域,因此高校的创新就很重要。第二,企业要关键技术升级,高校能给公司可以提供技术支撑。第三,高校为企业培养适配的人才。从大专生到硕士、博士,我们学校为江汽、奇瑞等培养了很多人才。合肥能把汽车产业发展起来,我们仍旧是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澎湃新闻: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结合您的经历,您怎么样看待这件事?
赵韩:人才能交流、能合作是好事。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差异,思路也是不同的,多一些思路更好。我们过去使用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是适应了当时比较落后、急于赶上的需求。所谓的集成创新,在追赶时期成效显著,且由于看得见易见效,更为政府部门所追捧。但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已追上发达国家,因此更需要原始创新。从教育上讲,这方面可向西方学习,形成合作互补。
赵韩:实际上早些年我就和省里提出汽车产业应该实施兼并重组,但新能源汽车发展延迟了汽车产业兼并重组的进程。整体产能提升后,增量只会慢慢的变少,这样肯定会淘汰一部分企业,兼并重组是必然的。
兼并重组就是这样,有必然的倒下和上升。利用兼并重组获取现有的优质资产很好,但如果兼并了一个做不好的也很麻烦。比如江淮,2000年后他们做得很好,我在做独立董事,和他们提到应思考在全国布局,收购一些优质资产,但当时没有实施,如果实施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另外,当时很多人提出将江淮汽车与奇瑞汽车合并,我表示反对,因为快速地发展时期不能合并,一折腾将影响二者的发展。而2015年后我提出二者可以合并,因为行业发展趋缓,合并后体量大一些,在采购、研发等方面会有优势,国家也会更重视,更加有助于发展。
澎湃新闻:现在合肥的六家整车厂(江淮、安凯、大众、蔚来、比亚迪、长安)体量很大,发展很快。
赵韩:如果产业链能在合肥形成集聚,减少相关成本、影响度增大、吸引产能,可能也会成功。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必须要深入具体了解企业,看它能不能做起来。也要看整体产业氛围,若能够做起来,对每个企业未来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澎湃新闻:怎么样看待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关系?比如特斯拉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作用。另外,合肥的汽车相关企业,比如比亚迪、国轩高科生产的产品很多运到海外,你怎么样看待车企出海?
赵韩:特斯拉确实起到“鲶鱼效应”,过去国内车企做新能源没那么大动力,但特斯拉就带来了动力,体现了国际对电动车的认可。国内也会觉得更有前景,企业更加发力去做这件事。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传统汽车技术已和国外差不多了。之前德国、日本的产品很好,但现在他们的工匠精神消失了,工业人才也较少。我们在供应链、全产业门类上有了优势,我觉得现在中国汽车是真的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了。
未来十年,我们的工业汽车竞争力会慢慢的强,所以“出海”是必然的。国家在这方面也要多做一些工作,因为国外政治、法律方面与国内有很大不同,我们的企业要搞清这些,才能避免风险。国家和省级政府应该组织一定力量瞭望全球市场,关注国际政策,为企业保驾护航。
澎湃新闻:还有就是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短期的企业压力,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从长期来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怎么来实现长远的、可持续的创新。
赵韩:政府喜欢干大事情,投入大项目,这是需要的,但如果仅关注大项目,后面怎么办?这几个搞不完了怎么办?大企业大部分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在政府、资本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慢慢做出一些成果。后续还要播撒一些能够发芽的种子,这是长线的东西,不能只集中在短线的、能看见效益的地方。
因为汽车产业链长、带动作用大,现在又加上新能源、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成为了一个万物互联的重要节点。未来它的带动能力还会继续扩大,产业链会更长。
有人说汽车是落后的传统工业,我不认同。汽车永远是高新技术产品。芯片、计算机、生物材料等几乎所有高新技术成果,最终都能应用在汽车上。
在可预见的未来,汽车不仅不会被替代,反而会是技术集成度最高的产品。它作为生产和生活工具,应用场景范围只会慢慢的广。
(本文执笔人吴英燕系澎湃研究所研究一部总监。浪尖“万亿之城2030”课题组由澎湃研究所、上海国有资本研究院联合组成,成员包括:张俊、罗新宇、吴英燕、吕娜、包青亚、王金涛、张志朋。特邀观察员商文芳。)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公众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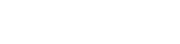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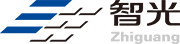





 2025.08.02
2025.08.02







